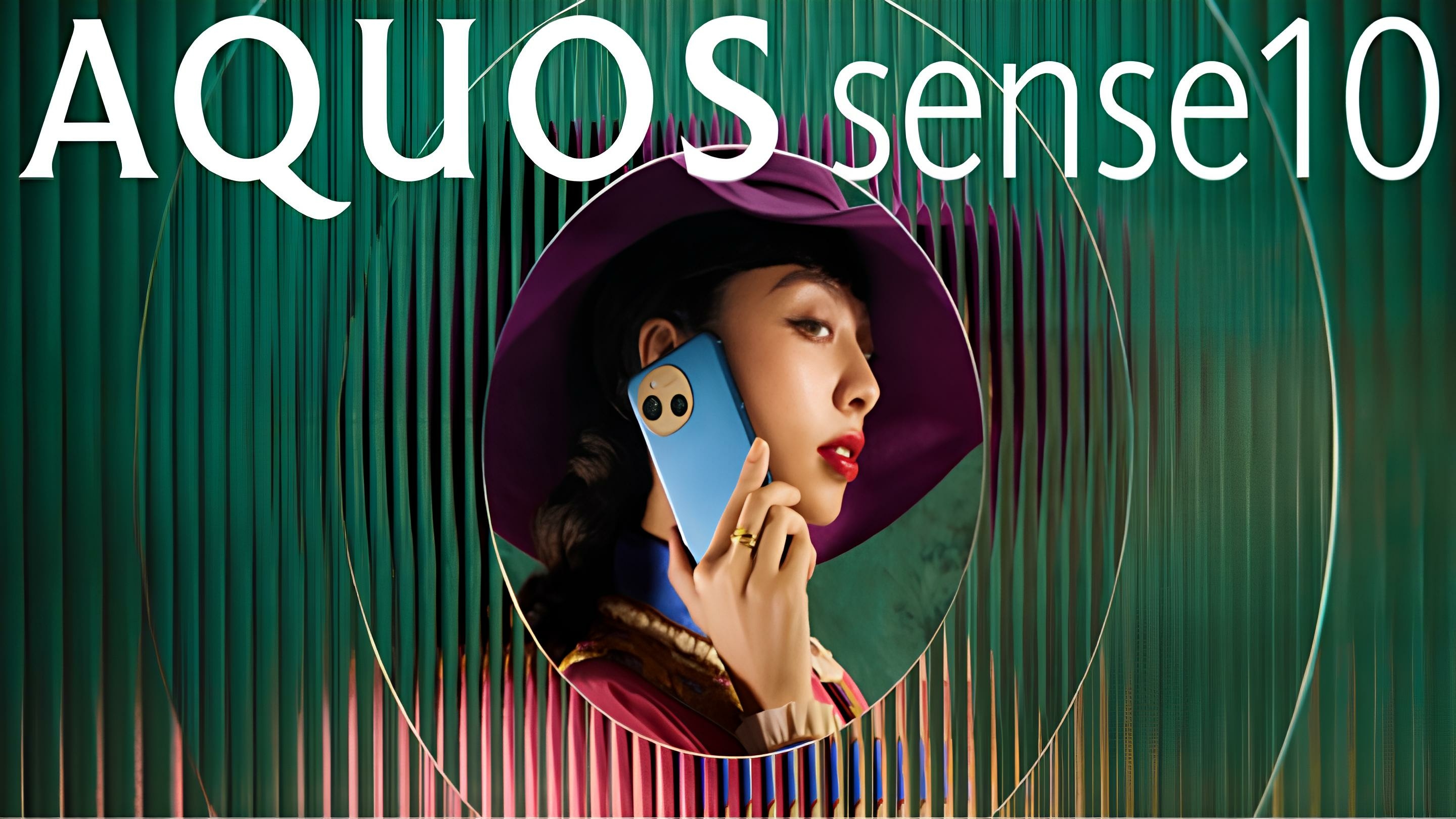圖:2005攝於當代館大門口 (更多圖片請見→ 當代館 )
公辦民營美術館的五年經驗
從台北當代藝術館面臨經營團隊約期即將屆滿談起
文/今藝術編輯部
 |
| 台北當代藝術館外觀。 (里歐諾) |
10月3日,當代館在仍無經營團隊投標的窘境下,由宏集團董事長施振榮捐贈給文化局的「500萬當代館開館經費」,於2001年5月辦了籌備處策劃的當代館開館展「輕且重的震撼」,成為一個已開館但仍無經營團隊的美術館。6月29日,由廣達集團董事長林百里及多位企業界、文化界董事以500萬元共組「財團法人當代藝術基金會」,7月,當代藝術基金會在作為唯一投標者的情況下獲得優先議價權,8月,文化局與基金會簽下五年合約,確立了當代館的經營。在沒有館長的情況下,由漢寶德暫代館長,賴瑛瑛任副館長。成為繼「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後另一個公辦民營、公私合資的文化機構,同時也是台灣美術館公辦民營之首例。
 |
| 台北當代藝術館館長謝素貞。 (吳垠慧) |
五年約期的適切性
目前謝素貞去意頗堅,而館員的去留則為其個人意志,會不會因為館長或經營團隊的可能異動而改變(甚至是整批離職),仍不確定。由於館長及館員的聘雇是由基金會決定,據了解,基金會方面希望整個團隊能繼續留下,而台北市文化局長廖咸浩,日前則特地赴當代館與館員會談,「表達最大的關心與支持」。但據了解,館員的意願仍不明確。
 |
| 台北市文化局局長廖咸浩。 (游崴) |
「我永遠都在準備後兩年的事」,謝素貞強調,「一個公辦民營的美術館只簽三、五年的約都是不適當的,就這點來說,政府並沒有真正了解公辦民營的意義在哪裡」,如果經營團隊、甚至是館的走向常常處於變動狀態,並有空窗期的可能,對於展覽計畫的貫徹,帶來的風險顯而易見。另方面,這也影響到工作團隊的異動,「這包括了經驗傳承的問題,當一個團隊要完全熟悉這個建築的使用,知道這個館的大小細節如電源、開關、建物問題等,都是需要練習的技巧。還有,原本招募的義工是不是會因此流失?你要逐漸再匯聚大家對這個館的信賴與依賴,這是需要時間的。」謝素貞表示。
 |
| 當代藝術基金會董事長林百里(右)、當代館館長謝素貞(中)及台北市長馬英九(左)於「非常厲害——設計中的藝術.藝術中的設計」展開幕現場。 (吳垠慧) |
 |
| 2004年8月的「虛擬的愛——當代新異術」展,創下當代館開館至今最多參觀人次的紀錄。 (台北當代藝術館) |
營收與文化影響力
依照當代藝術基金會當時與文化局簽約內容,當代館一年的經費由基金會出資約51%、文化局出資49%,各為2,500萬及2,400萬。而館的支出中,人事、硬體維護等行政支出,與展覽、教育推廣等業務支出約各佔一半。謝素貞強調:「即便目前政府給的這2,400萬已是最高的支持金額,但這筆錢卻只夠剛好用來維護這個古蹟建築物使它正常而已」,其餘的營運費必須由基金會來出,基金會所出的錢必須靠美術館的營收來打平,甚至賺錢。「那是不可能的。」謝素貞斬釘截鐵表示。
當代館自開館以來,除了少數幾檔如「虛擬的愛——當代新異術」等曾帶來洶湧的參觀人潮外,其餘展覽的門票收益大多差強人意。而在另一方面,當代館的賣店早在2002年5月約期屆滿後即結束便無繼續,而咖啡店目前則為外包,由當代館租場地給外面商家經營,當代館只收租金,如營收到達一定水準,將會有一部份回饋金給基金會與文化局,但由於營運仍未達一定水準,故目前只收租金。依此狀況,當代館確實很難在單靠盈收的狀況下而自給自足。對此,文化局長廖咸浩雖認為當代藝術從本質上來說本來就很難吸引大量人潮,但也坦言「當代館在行銷上是可以再加強」。
這確實關聯到屬於文化事業的美術館,在公辦民營的狀況下所遭遇的商業性行銷與理想性格的問題。究竟要如何兼顧二者是當代館公辦民營必須努力的目標。「公辦民營模式還沒有結論,都只是剛開始而已」,謝素貞並不想遽下斷語,但目前看來,她是頗為保留的。「我覺得政府的好意有、民間的好意也有,但事實不允許。專業美術館其實不能用公辦民營的模式來辦,一些觀光型的館可以這樣做,會賺翻,如宮崎駿美術館。但專業美術館不可能,我們辦一個好展覽800萬到1200萬,但門票卻只收50元,多少參觀民眾把這個樓踩平了都無法平衡營收,在沒有平衡的情況下,你認為有多少財團會願意一直投錢進來?文化是深耕的事情,沒有資金的長期投入,是無法深耕的」。對於市政府目前新規劃的多媒體藝術中心也將行之以公辦民營模式,謝素貞也是不表樂觀,她強調:數位藝術high-maintain的本質,根本就很難僅僅靠餐飲與門票就打平。
對於一個「好展覽」,謝素貞相信不是票房問題,「我一直認為美術館不是遊樂園、不是動物園,所以我不用『營收』兩個字,我只會問『你覺得這個展好不好?』,因為口碑好的展覽絕對不是賣票賣得好不好的問題,它是會留在你心裡面的」。對謝素貞而言,這是一種影響力,相較於造成轟動的「虛擬的愛」,她更想強調「城市謠言——華人建築展2004」:雖然展覽的門票營收不高,但在亞洲卻有指標意義,「透過這15位參展建築師,它的影響力在於我們都會景觀的改變,這是我說的投資報酬率」。
公辦民營不應只為減少政府支出
 |
| 2004年11月「城市謠言——華人建築2004」展覽現場,圖為劉國滄作品。 (劉國滄) |
謝素貞也認為:台灣的公辦民營模式都是學習自日本的經驗,但她強調日本目前五千多間美術館,也僅有約十間是以此方式經營,它的可行性其實是待評估的,「我們為何要當代館?如果公辦民營化,適合台灣嗎?適合的是美術館還是表演廳?除此之外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這應該是我們要去探討的,而不是貿然採用一個別國家尚未實行有成果的方式,僅僅是為了減少政府的支出」。
當代館作為台灣第一個公辦民營美術館,它帶來的經驗是重要的,但五年的觀察時間顯然仍是太短。在政府現正熱烈進行中的多媒體藝術中心,也即將採取公辦民營模式之時,當代館於此變動時刻,丟出來的疑問將值得深思。
註1:蔡珊珊,《博物館公辦民營以委託基金會營運模式之研究——以台北當代藝術館為例》,碩士論文,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2003.06,頁97。
註2:引自蔡珊珊對陸蓉之的訪談。同前註,頁118。
註3:謝東山,〈文化經營事業豈可短視——北美二館不宜內製外包〉,《典藏.今藝術》,90期(2000.03),頁102-103。
日期:2005‧11
出處:今藝術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